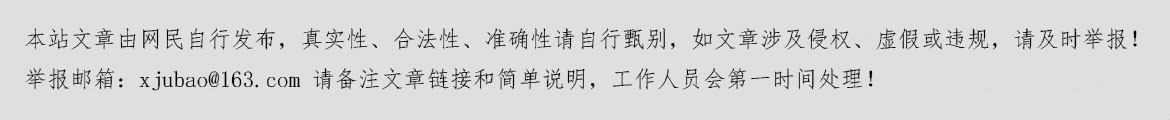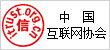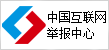为什么《沙丘》被搞砸了?
2022-03-17 03:33:02
搜影视在线看最火影视 https://www.souys.cc
近期最热门的电影应该就是丹尼斯·维伦纽瓦导演的《沙丘》了,按照目前的趋势看,这版《沙丘》打破了扑街的命运。
号称科幻界最难改编的小说在之前让很多导演遭遇滑铁卢,大卫·林奇就是其中之一。
大卫·林奇(David Lynch),美国导演、编剧、制作人
早在1984年,林奇就拍过一版《沙丘》,对林奇来说,这部电影可能算作他人生的“污点”,口碑扑穿地心。甚至在拍摄之前,林奇压根儿都没听说这部小说。
电影团队把拍摄地选在了墨西哥,拍摄场地非常“豪横”:有8个巨大的摄影棚,至少80个布景,4个摄制组工作。林奇说“那些现场布景太**漂亮了!”他找了辆三轮车,每天骑着车在片场间穿梭查看拍摄情况。
林奇没有拿到最终剪辑权,片方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排片,要求林奇必须把电影剪辑到2个小时17分钟之内。对这样一部史诗巨作,在这么短的片长中讲故事,显然很难实现。
当年不到40岁的精神小伙林奇被折磨得要疯掉,以至于后来拒绝承认《沙丘》是自己的电影:“《沙丘》是场噩梦。”
导演佐杜洛夫斯基(也拍过一版《沙丘》,没能成片)看完林奇的《沙丘》后幸灾乐祸:“我开始变得很开心,因为那部电影太糟了。”
那这部电影究竟是怎么搞砸的呢?林奇“有话要说”。
《沙丘》是场噩梦
我听说迪诺·德·劳伦蒂斯(电影制片人)想和我见面聊聊一个叫《沙丘》的片子。我以为他说的是“六月”(June,发音与Dune相近),因为我对《沙丘》一窍不通。但我的朋友全都说:“我的天哪,这可是全世界头号科幻小说。”所以我想:好吧,我就去见见迪诺。
《沙丘》是个关于寻求启蒙的故事,这是我想要拍摄它的部分原因,但我也知道接下《沙丘》有某种命中注定的理由。虽然我不清楚这理由究竟是什么,我还是接下了。我让克里斯·德沃尔和艾瑞克·伯格伦来与我一起写剧本,因为我们曾经共事过,我很喜欢他们俩,而且他们也是这本书的狂热粉丝。
克里斯、艾瑞克、迪诺的儿子费德里科(Federico)和我一起,到汤森港和弗兰克·赫伯特待了一天。弗兰克和他妻子贝弗利(Beverly)都很和善,我们聊了很久。我都不记得当时是不是聊到了这本书。
越深入这本书,我发现它越复杂。但是迪诺这个那个都不想要,我就知道很难让这个故事自圆其说。这儿有个屏蔽墙,那儿有个屏蔽板,然后是来自这种文化的一些元素和来自那种文化的一些元素,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圣战和其他好多事情,非常复杂。不过,和弗兰克·赫伯特待在一起的那天很不错。
那天晚些时候,我搭飞机回洛杉矶,费德里科则要从西雅图转机去阿拉斯加。我的飞机先起飞,所以他一直陪我走到舱门,真是很好心。他们说,费德里科那么帅,女人看到他就被迷死了。在去阿拉斯加的路上,费德里科认识了一位命中注定要认识的飞行员,那年7月,他们俩就在一场空难中共同丧命。
一旦开始和克里斯以及艾瑞克共同创作剧本,我很快就意识到我们仨头脑里对《沙丘》有着全然不同的概念。那时候我已经知道了迪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而且我知道,如果按照克里斯和艾瑞克的方式写剧本,我们最终只会空忙一场,因为迪诺绝对不会同意。迪诺不懂任何的抽象概念和诗意——他就想要大量的动作场面。克里斯和艾瑞克离开的时候我感觉很糟,因为他们都指望着能靠《沙丘》赚一笔钱,但我还是自己一个人继续把剧本写完了。
除了喜欢和“我看不懂”之外,我不记得迪诺还对剧本发表过任何其他意见。他绝对不会提出创意,他只会对既存的事情有所反应。迪诺想挣钱,对此我也没有意见——迪诺就是这么个人。
我们先是在洛杉矶和纽约寻找扮演保罗·亚崔迪的演员,但没找到合适的人选。于是迪诺说:“好吧,现在咱们得在二线城市找了。”西雅图的一个女人推荐了凯尔,还寄来一张照片。一来二去,凯尔来了,在我见过的所有人中数他最为出众。事情就是这样。
凯尔是个很棒的人,同时也是个很棒的演员。凯尔兼备这两项优点。之后他到贝弗利山酒店九号“片房”(boongalow,平房的意大利口音发音)见迪诺。他总是住在同一间房里,那是个巨大的“片房”,迪诺总是这么叫它。见面后,迪诺测试了凯尔,他表现得很不错。接着他又让凯尔脱了上衣,测试了几个打斗动作,想看看他打斗时的样——你知道的,意大利动作片,男子健美照那一套。凯尔照做了,然后他就拿到了这个角色。
拉法艾拉和我当时正在查看墨西哥丘鲁武斯科制片厂(Churubusco Studios)。她雇了个中东人,开直升机带我们四处查看,寻找能拍摄电影中外星风景的场地。那架直升机非常大,他带我们到了一个地方,目之所及全都是黑色火山岩,其中星星点点钻出些绿色仙人掌。那儿真的很古怪,但怪得很漂亮。
我们在丘鲁武斯科制片厂的时候,我在餐厅里见到了奥尔多·雷(Aldo Ray),觉得他是扮演格尼·哈莱克(Gurney Halleck)的完美人选。我跟他聊了聊,告诉他我想让他出演这样一个角色,他非常高兴。迪诺听说我想用奥尔多·雷后却说:“他就是个酒鬼。”我说:“咱们让他来试一试——他真的是个完美人选。”于是奥尔多带着他儿子艾瑞克来了,那时候艾瑞克差不多17岁。(演员艾瑞克·达·雷(Eric Da Re)后来出演了前两季《双峰》。)
那天早上到了制片厂,有人告诉我“奥尔多在化妆间里”。于是我就过去了。当时差不多是早上八点半或者九点,奥尔多瘫在沙发上,因为他喝了一晚上酒,而可怜的艾瑞克羞愧地坐在房间另一头,低垂着脑袋。我拿了把椅子坐在奥尔多面前,问:“奥尔多,你能演吗?”然后他说:“不能。
我们勘察了许多景,想找一个适合拍这部电影的地方,最终迪诺找到了最便宜的选择,也就是墨西哥。那些日子里的墨西哥真是个完美的地方。墨西哥城是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城市。亲眼见到之前,没人会相信我说的话,但一旦亲眼见到,他们就会说:没错,你说的对。首先,城里的光线和色彩那么梦幻。到了晚上,天空一片漆黑,而小灯泡照亮着漂亮的绿色、粉色或黄色墙壁。墨西哥的建筑都是彩色的,还带有一种经由岁月洗刷的光泽感。到了晚上,所有东西都是黑的。但光照在墙上的地方,会产生许多长方形的小彩条。
那真是个充满诗意的城市,那里的年轻画家们也创作着不可思议的东西。毒品集团还没产生,人们善良又随和,虽然他们的政治领袖不可一世,正折磨着他们,偷走他们所有的钱。如果一位总统在选举中失利,他就会把所有的钱卷走,在西班牙盖一座城堡,然而大家好像都接受了这样的现实。
我不知道迪诺究竟来没来过丘鲁武斯科——我不记得在现场看到过他——但拉法艾拉代替他在片场发号施令,因为他们俩那么像,就像用同一块布料剪裁出的两件衣服。拉法艾拉真是个人物。她超级聪明,不说废话,也不瞎胡扯,是个强大的制片人,就像女版的迪诺,我爱拉法艾拉。工作人员来自天南海北,有意大利人、英国人、德国人,还有一些西班牙人——各种各样的人,片场还有很多酒鬼,当然少不了派对。
林奇与《沙丘》中的小演员
有一次我回到家已经特别晚了,得给玛丽打个电话,但我醉得太厉害,不知道为什么穿着衣服躺进了浴缸。我不记得自己为什么坐在浴缸里,但我后背靠着浴缸沿,抱着电话,必须全神贯注才能拨下每个号码。然后我闭上眼,必须非常集中精力,才能让自己和玛丽说话的时候听起来不是一摊烂醉。我搞定了,但挂电话之后就吐了。
查理·鲁茨告诉我,在墨西哥洗澡的时候,应该先啜一口伏特加,把酒留在嘴里,然后去冲澡,冲完后再把伏特加吐出来。要不然冲澡时水会流进嘴里,你就会不知不觉把水喝掉。我每天早上都照做,一次也没生病,其他人却全生病了。拉法艾拉说,每天都会有半个摄制组的人请假,因为总有人在生病。
丘鲁武斯科当时有八个巨大的摄影棚——现在其中四个已经让位给了住宅和其他建筑——我们的人可是这些的两倍。丘鲁武斯科占了很大一块地,于是我找了辆三轮车。我很喜欢它,每天骑着车在片场间穿梭查看拍摄情况。
我总是跑个不停,因为有四个摄制组在同时工作。简直疯了。那些现场布景太他妈漂亮了!墨西哥的手艺人很了不起,布景从背面看上去就和从正面看上去一样好。他们是用雨林中的柳安桃花心木搭建的——真是难以置信。至少有80个布景,有些制作得非常精细。托尼·马斯特斯干得真漂亮。他会从零开始,像变戏法一样做出件神奇的东西。他想让布景设计看起来更有科幻感。
那次威尼斯之旅(与制片人一起去威尼斯的旅行)对我影响很大。我总是对托尼讲起那次经历,逐渐地,布景风格也开始往那个方向转变。电影中的飞船是一顶一地棒。它们某种程度上把青铜、银、紫铜、黄铜和铅锡锑合金融合在了一起,再混上点金子,真是让人震惊。卡洛·兰巴尔迪设计了公会领航员。我想让他看起来像只巨大的蚱蜢。我在剧本里就是这么写的,而且最初也是和卡洛这么交代的。但人很奇怪:如果看看外星人E.T.的脸,你能从上面找到卡洛·兰巴尔迪的影子。人们总是在塑造他们自己,所以公会领航员的脸看起来也有点像卡洛·兰巴尔迪。
迪诺雇了个叫巴里·诺兰(Barry Nolan)的人做特效摄影。巴里很不错,因为他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考虑到他拿的那点工资,可以说他相当完美地完成了任务。在巴里之前,迪诺面试了好多人,只有巴里要价最低——没准迪诺还对他施了压,进一步压低了价格,所以巴里从头到尾可能几乎没赚到钱。迪诺能把人的血都榨干,只剩下一把骨头。
设计哈肯尼的世界太有意思了,因为他们居住在一个工业世界里。哈肯尼不建屋顶,可以直望进宇宙的一片漆黑之中,火车停在上面的站台上,非常酷。哈肯尼男爵能飘起来越墙而过——而且是飞过非常高的墙。
有一次我们正在拍哈肯尼男爵的一场戏,摄影棚里大概有60个人,现场还竖立着至少有30米高的巨大墙壁,真的非常大。那是个真刀实枪的大场面。两个镜头之间的休息时间里,大家正在四处乱逛,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大的撞击声!几个大钳子从空中的窄道上掉下来了,如果砸到人会出人命的。然后我们听到头顶很高处有人逃跑的声音—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会被炒鱿鱼的。
电影中的哈肯尼男爵
我们要拍摄一场需要动作控制的戏,意思是同一个镜头必须拍好几次,每次都要一模一样。有专门用电脑和机器做动作控制的人,这样就可以直接复制镜头,保证每次都一样。但我们身在墨西哥城,身边没有这样的人。我们要拍的这个场景需要用到一辆移动的手推车和一个摇臂,我回过头去看他们准备的动作控制装备,就像是放在滑轨上的儿童车一样。断断续续的滑轨,地板上布满灰尘,那辆小儿童车则是用创口贴、电灯线和裸铜丝做的。摇臂也是穷人那一套——泡泡糖、橡皮筋和几根棍子,这就是我们的动作控制摇臂!效果还不错,但在你想象中,一部400万美元制作的电影可不是这样的。
布拉德·杜里夫说的没错。在一场戏中,我确实希望尤尔根·普洛斯诺(Jürgen Prochnow)能动个手术。我跟尤尔根说了,但他应该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但你知道,我摸了摸自己的脸颊,觉得那儿没多少肉,穿个小孔不算什么特别极端的事吧!但听听接下来发生的故事。莱托公爵,也就是尤尔根,躺在桌子上,他嘴里有颗毒牙,只能通过打破毒牙释放毒气来杀死哈肯尼男爵。但此时他正病着,神志不太清楚。
我们做了个小摇臂来拍这个场景,但只能从一个固定角度拍,因为有跟管子沿着尤尔根脸颊的一侧升上来,接着拐了个弯进入他嘴里,然后再拐个弯,沿着另一侧脸颊下去,整个装置用胶条固定在了他脸上。我们只能从看不到管子的一侧拍摄,但你能看到毒气腾起,就这么拍完了第一条。他躺在那里,蜷缩起身体,接着喷出了彩色毒气。这条挺不错。
但刚拍完,尤尔根立刻跳了起来,尖叫着撕掉了脸上的东西,然后冲出了片场。他跑进自己的拖车里,怎么也不肯出来,快要气疯了。原来从管子里喷出的蒸汽还是烫的,管子被弄得更烫,烧坏了他的脸。我只能跑到他的拖车里劝他冷静下来,一再向他道歉。不过他说什么也不肯拍第二次了,所以我们最终用的就是第一条。
电影拍摄完成后,我又在墨西哥待了一阵,总共在那里待了一年半的时间,然后我们回到洛杉矶做剪辑。剪辑《沙丘》的六个月中,我在西木区(Westwood)找了三四个住处。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在不停地换地方。我一点都不讨厌墨西哥,回到洛杉矶后我反而有点发疯了。
因为一到剪辑室,我们就发现墙上已经写了清楚的剪辑说明。太可怕了,真的很可怕。必须剪出一部符合2小时17分钟时长要求的电影,那就像是场噩梦。许多东西被截短了,还加上了絮絮叨叨的画外音,因为他们都觉得观众可能会看不明白。有些画外音真的不该加,有些特别重要的场景也被舍弃了。可怕,但事情就是这样的。对迪诺来说,这部电影存在的目的就是赚钱。这是在做生意,假如长于2小时17分钟,电影院就会相应减少放映场次。这就是他的逻辑,你必须按照这个时长要求来剪,别管剪出来的是不是垃圾。
我很爱迪诺。迪诺这个人很棒,他对我就像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我喜欢这家人,也喜欢和他们待在一起。但他考虑事情的方式和我完全不同,就像是你花很大功夫画了幅画,结果有人进来把画剪掉几块扔了,那它就不再是你创作的那幅画了。同理,《沙丘》也不是我的电影了。
林奇版《沙丘》海报
电影最终剪辑完成后,我们举行了一场派对,玛丽也来参加了。派对上有几个女孩打了起来。我不知道有多严重,但真的是动手了。后来电影在白宫上映,我和玛丽·菲斯科、拉法艾拉以及拉法艾拉的丈夫一起去了白宫。玛丽和我见到了南希和罗纳德·里根,里根对《沙丘》真的很感兴趣,和我聊了半天电影以及其他事情,后来我们都开始跳舞。我屏蔽了坐在那里看完整部电影的记忆,也没读过任何关于电影的评论。
过了不久,他们想让我剪辑一部电视版《沙丘》,但我拒绝了。我没看过那一版,也不想看——只知道他们又加入了一些我拍的画面,配上了新的画外音。我曾经想过,如果我有机会看完我拍摄的所有镜头,并剪出我自己的《沙丘》,它会是什么样呢?
但我自始至终都知道迪诺拥有《沙丘》的最终剪辑权,所以在开拍之前,我其实已经出卖了这部电影。我知道他会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我都是按照他的喜好拍的。想想真可悲,但只有这样我才能生存,因为我签了合同。《沙丘》三部曲,原本还要拍两部续集的。假如第一部大卖,我们接着拍下去,我就会变成“沙丘先生”。
我拍《沙丘》的时候,玛丽带着奥斯汀搬到了弗吉尼亚,她这么做很有道理。玛丽的妈妈是做房地产的,她找到了一栋特别划算的房子。而且杰克和茜茜的农场也在那附近,我又不在家,我猜玛丽是想住得离她妈妈近一点吧。那个地方挺棒的,拍完《沙丘》后我们就住在那里。
到弗吉尼亚的时候,我整个人非常虚弱——经历了那么多让人神经紧张的时刻,经历了那么多失败。我记得有天我们在草地上散步,看到了一些植物。它们不算是野草,样子介于野草和树木之间。它们成簇生长,每簇直径大概2.5厘米,有三四米高,瘦弱的小东西。
我不喜欢这种植物,于是从我们坐着的地方站起身来,抓住一根往外一拉,就把它连根拔出来了。我想着应该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部拔掉,于是抓住两根,又拔出来了。接着我抓住了五根,用力一拉的时候,我感觉到后背有什么东西撕裂了。那五根没拔出来,我放弃了。
当时并没有觉得很疼,我还坐回去继续和玛丽聊天,但聊完天后,我发现自己站不起来了。那天晚上玛丽想让我去和奥斯汀说晚安,我撑住后背,几乎是把自己推出了房间,穿过门厅来到奥斯汀的卧室,看见他已经躺在了床上。我把自己推到床边,躺在地板上给他讲了个睡前故事。然后我又把自己推回卧室,在让人龇牙咧嘴的疼痛中钻进被子里,之后四天没下床,因为我动不了了。
第二天来了个医生,他告诉我拉伤了一组背部肌肉,要很长时间才能痊愈。这部电影真是在许多方面消耗了我。不过,虽然《沙丘》是场噩梦,但能借此认识迪诺和他的家人也算值得。而且,没有这部电影,就不会有《蓝丝绒》。
本文节选自
《梦市:大卫·林奇传》
作者: [美]大卫·林奇、[美] 克里 斯汀·麦肯纳
译者: 胡阳潇潇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理想国
出版年: 2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