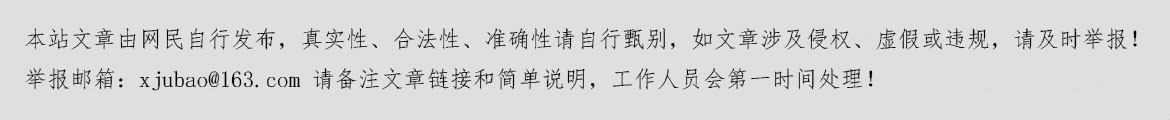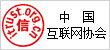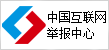我带她去了宾馆,为什么同样是女人,她和妻子的感觉如此不同?
2021-09-17 15:52:02
3月的一个上午,我在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怯生生的男声:“请问您这儿可以做心理咨询吗?”没有等我回答,他又接着说:“我有个同事,感情上遇到了一些问题,很苦恼。”“可以啊,他要是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约个时间聊聊。”我笑着说,于是我们在电话里约好了时间,就在我要放下电话的那一瞬间,对方突然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对不起,我骗了你,其实我就是那个人,我叫张扬。”
第二天下午,我看见了张扬——白衬衫、牛仔裤、略带腼腆的神情,看起来像是一个初涉世事的大学生,我把这种感觉告诉了他,他立即摇摇头:“其实我18岁就来北京读大学了,接着读了研究生,毕业后在大学里做了两年老师,后来下了海,现在自己开了一家公关策划公司——算得上是一个老江湖了。”他耸了耸肩膀,故作老成的样子反倒让我觉得他更像一个学生了。
张扬自述:2000年,经人介绍,我认识了应红,第一次看见应红是在她家里,当时已经是下午两三点了,我还没有吃饭,她很自然地去厨房给我煮了一碗面条,微笑着坐在我面前看着我吃,那种笑容给人的感觉,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如沐春风”,后来她看见我衬衫上有一个扣子快掉了,又找来针线给我缝,记得她的脸当时离我很近,说实话那是我第一次和一位异性离得这么近,但我心里没有紧张和激动,只是有一种温暖和踏实的感觉,就像在母亲身边,是的,就像沐浴着母爱的光辉一样——我从小生活在一个经济拮据的家庭,母亲劳于生计根本无暇顾及我,所以家庭的温情一直是我非常缺乏又非常向往的,而应红恰恰能给我这种温情。就这样,在仅仅交往了两个月以后,我和应红就结婚了。婚后的生活应该算是幸福的吧,应红将家里的一切料理得井井有条,她对我也很体贴,像照顾孩子一样将我照顾得无微不至。
2003年下半年,有一天我很难得有一些空闲的时间,鬼使神差般地上网聊起天来——以前我一直是很不屑于做这种事的。就是通过这次聊天,我认识了“四月”,和“四月”聊天让我感到非常新奇和兴奋,她几乎可以在任何话题任何层面上和我并驾齐驱,我从未见过像她那样的女人——聪明、幽默、灵慧又不乏柔情。从那以后我迷上了上网聊天,确切地说是迷上了和“四月”聊天,有哪一天不聊心里就空落落的,甚至,我会把每天上网聊天当作对自己辛苦工作一天的最好犒赏。
随着聊天的逐步深入,我和“四月”慢慢都知道了彼此的真实情况,我知道了她真实的名字叫“李晓娅”,是上海一家外企的白领,离异后带着五岁的女儿独自生活,比我大八岁……我们开始了长时间的在电话里的交谈,她成了我心中一份秘密的牵挂,我会随时随地想起她,比如刷牙的时候,开车的时候,给员工开会的时候,我都会想:她现在在做什么呢?
晓娅经常来北京出差,但我们谁也没有提出来见见面——或许是因为我们都明白彼此之间有无法逾越的障碍,更明白一旦见了面也许情感的闸门就会轰然而开,一切会变得无法收拾,我第一次体会到了爱情的甜蜜与痛苦,还有那种想摧毁一切的冲动。2001年1月8号,我的生日,快下班的时候,我接到晓娅的电话,她兴奋地说祝你生日快乐你现在往窗子外面看看那个站在广场上穿着白大衣的女人就是我,我冲到窗子前探出身去,看见晓娅正握着手机向我挥手——她真的很漂亮。那个晚上,我带晓娅去了宾馆,我们做爱,很投入很尽兴,彼此都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我真的很奇怪,为什么同样是女人,应红和晓娅给我的感觉会如此的不一样。
我彻底地陷入与晓娅的爱情里,一刻也不能忍受没有她的日子,常常上午上着班,下午就买了张机票飞到上海去看她,最多的时候我一个月花在机票上的钱就有几万元。同时,我一天比一天地不能面对应红,她还是那样一心一意地照顾我,每次我看着她那一脸满足的笑容,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儿,我不得不编出各种谎话来欺骗她,这让我感觉非常不好,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猥琐的男人,我常常做恶梦,梦见应红割腕自杀了,血流了一地,我总是一身冷汗地惊醒过来……一边是我爱的女人,一边是爱我的女人,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办呢?
“您说我该怎么办呢?”身为一名心理医生,我曾经无数次地面对这样的提问,问的人一脸的无助与无辜,像一只迷路的羔羊,期望我能给他们指出一条路,但事实上我从未给任何人作过此类的指点,只因我明白世界上的许多问题尤其是感情问题都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答案,也因我个人的性格、价值观、教育背景和成长历程与前来做心理咨询的人并不一样,所以我不可能以我的立场来为他们作出选择,更不能以社会的道德标准与价值取向来对他们评头论足——心理医生不是引路人,他(她)更像是同行者,与人分享和共担,教会人学会分析自我了解自身,从而能自己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答案。
我问张扬:“对现在这段感情,你是想让它慢慢淡化,或者是保持现状,还是想进一步发展?”他脱口而出:“我当然是想离婚了,但我不知道怎么和应红说,她还什么都不知道,老这样欺骗她我觉得很内疚——我现在最烦的就是这个。”“那你觉得能瞒得住她吗?你内心能承受得住内疚感的折磨吗?如果不能,你妻子知道以后会是什么反应?”张扬沉吟片刻,叹了一口气:“时间长了肯定是瞒不住的,迟早的事,我觉得如果我主动和她说了,她受到的伤害可能会小些,我自己的心理负担也可以放下了,要不然我真的快崩溃了……”这次心理咨询的结果是张扬决定向应红坦白,坦白后的结果一如他所料——应红说什么也不肯离婚。张扬另外租了房子搬了出去,应红在家里整日以泪洗面,她的状态很让张扬担心,于是将我推荐给了她。
应红在一个微雨的午后来找我,她是那种典型的北方女子,身材高大而丰满,脸上的表情一如窗外阴郁的天气,她低着头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一直很不安地摆弄着手里雨伞的伞柄。
应红自述:过得好好的日子,我不明白他怎么舍得将这个家毁掉,现在这个世界好像谁狠得下心谁不道德谁就厉害,我想不通。
对张扬我可以说做得无可挑剔,说出来你可能都不相信,因为我个子比他高,为了我们走在一起般配,我就把我的高跟鞋全部都送了人,再也没穿过。我真的是很爱他的,而且我们一直都挺好的呀,他公司的人都说他是“模范丈夫”,他特别恋家,有时候谈完公事都晚上八九点了,别人请他吃晚饭他都会推辞,一定要赶回家来和我一起吃。
他说和那个女人有说不完的话,和我却没话说,但是过日子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肯定会有没话说的时候,而且人家会心甘情愿和你过一辈子吗?人家会任劳任怨地为你打理一切吗?他怎么也不想想!反正我现在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鬼迷心窍似的……我跟他说:你不要逼我,逼急了我什么都干得出来,大不了大家同归于尽,我倒不是吓唬他,你说你那么真心对待的人都会背叛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诉说的过程里应红的泪水不断地往下淌,精神处于近乎歇斯底里的状态,她不停地说着,我知道这些话连同不平和委屈一定是她压抑在心里很久的,我一直温和地看着她,用心倾听,希望能够通过我的眼神和语气让她明白:我愿意听她诉说,我能体会她的感受——我想这会让她心里舒服一些。
等应红稍微平静下来,我试图帮助她整理一下自己混乱的情绪,我问她:“依你对张扬的了解,你认为他会坚持和你离婚吗?如果他坚持和你离婚,你是不是就真的无法面对今后的人生了?”应红想了想,告诉我:“我觉得我还是挺了解张扬的,别看他在社会上也有几年了,其实一直生活在一个很单纯的环境里,所以在遇到诱惑时就没有免疫力,我觉得他这会儿就是一时糊涂,早晚会明白的,我愿意等他。”“既然你不想离婚,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们曾有过那么好的时候,但后来却让别人有机可乘,这其间有没有一些原因?”我又问她,“我也不明白呀,我自己也纳闷呢!”应红一脸的茫然。
通常,在一场婚外情里,受伤害的一方往往沉浸在自怜自伤的情绪里无法自拔,他们始终不能跳出来对自己的婚姻作出理性的思考,应红即是如此。我说:“这样吧,我们来做个小实验,你先平静一下,深呼吸,然后闭上眼睛,把自己当成张扬,跟着我的叙述来感受感受。”应红按照我说的闭上了眼睛,我根据张扬曾经给我描述的他们家庭生活的片断,用平缓的语气开始了叙述:“今天,你与一家日本公司的生意遇到了一些麻烦,你很烦,这种烦和员工又不好说,偏偏你又没什么朋友,于是你想下班回家后和应红说说。一到家,你往沙发上一躺,很希望应红来问问你:‘怎么样?今天工作还顺利吗?’”
但此刻她却一个劲地催促:‘你看你一回家就往沙发上一躺,快起来,洗洗手准备吃饭!’你不情愿地起来,心里很纳闷为什么在应红眼里吃饭永远是头等大事。饭桌上本来是聊天的好时候,可应红却把电视打开了,她一边瞄着电视里的言情剧一边不停地往你碗里夹菜:‘吃,吃,你爱吃的炖牛肉,怎么不吃呀?特为你做的。’吃完晚饭,应红又忙着洗碗,收拾厨房,你到底忍不住了,倚在厨房的门框上说:‘今天真烦,就是给那家日本公司在中国办展览的事,唉,这帮日本人真不好打交道——’‘得得得,我最讨厌日本人了,快别和我提他们,哎,你站在这儿干嘛呀,快洗澡去,水给你热上了,这会儿正好,快去!’应红打断了你的话,你看着她忙碌的身影,看着这个整洁得没有人气的房子,有一种空荡荡的令人绝望的孤独……”
在我叙述的过程里应红的神情一变再变,最后她睁开眼睛,目光定定地落在书架的顶上,很久很久,她突然很放松地笑了,那是我在整个咨询过程里第一次见到她的笑容,她起身握住我的手,认真地说:“郑教授,我明白了,让我回去试着改改看吧。”
这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应红,倒是张扬经常来,对我倾诉着对李晓娅的痴迷和对离婚的渴望,他的狂热暴露了他心理上的不成熟,但我时时刻刻提醒着自己不要对他下判断也不能替他做决定,作为心理医生,我信奉这样一个原则:任何人的心里都有各种结,能真正解开这些结的人只能是他(她)自己,在当事人艰难地寻求解脱的过程里,心理医生扮演的只是(也只能是)一个启发者的角色。
对张扬,我只能给他提供一个倾诉的空间,并且帮助他从牛角尖里钻出来,能够全面、发展地去看问题——这样他才能明白在任何事情的走向上,其实是存在着很多种可能很多个方向的。比如我会问他你一旦离婚了,李晓娅是不是愿意和你结婚?如果她愿意和你结婚,你们之间年龄的差距会不会成为你们生活的障碍?即使现在不会,但十年以后呢二十年以后呢?还有李晓娅的女儿会不会接受你?你们以后还要不要孩子?如果你们不想要,你的父母会同意吗——他们就你这么一个儿子?等等。后来张扬告诉我,他曾经就结婚的事情问过李晓娅,但她一直没有给他承诺。
事情发生戏剧性的转折,是有一次张扬去上海看望李晓娅,在她卧室里发现另外一个男人的袜子。张扬从一个爱的顶点迅速地登上一个恨的顶点,这一次受伤害的人成了他,他频繁地给我打电话如祥林嫂一般反复表达着自己的愤怒,我告诉他:“这时候你就运用一下在书本上学了多少年的辩证法吧,世界上的事情总有利弊的两面,同样的人,他(她)有美好的一面,肯定也会有不那么美好的一面,所以你大可不必为曾经的付出觉得不值得,也不必为自己的失去而痛苦。”
年底,张扬打电话告诉我他已经和应红重归于好,并且已搬回了家里,而应红正在积极复习,准备报考研究生。元旦,我分别收到张扬和应红寄给我的贺卡,张扬写的是:就让我把过去的一切,当作一场已逝的梦吧,梦醒了,我会更珍惜家庭。应红写的是:我现在才明白,在两个人的爱情园地里,只有永不懈怠的耕耘,才会赢得满园迎风盛放的花朵,从来就没有永不凋谢的花朵,正如从来就没有一劳永逸的婚姻。
事情到这里似乎是皆大欢喜,但我深知:生活总是起伏着向前,每一个平缓处都暗藏着突变的潜流,因而危机无处不在,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个人经过这一场感情的变故,彼此在心理上都获得了成长——这将有利于他们更好地去面对今后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本文选自《心理咨询师手记》,作者卡玛,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